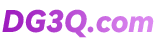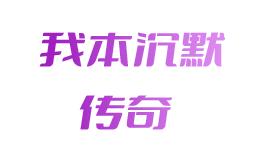
1997.04.11
本来我不想写什么纪念的文章。因为昨天是王小波逝世十周年的时间。博客首页里到处都是纪念他的人。我觉得这样的纪念没有实际意义,不如多花些时间读他的书,这才是真正的纪念。对他灵魂的真正告慰。刚才听了西辞唱的
本来我不想写什么纪念的文章。因为昨天是王小波逝世十周年的时间。博客首页里到处都是纪念他的人。我觉得这样的纪念没有实际意义,不如多花些时间读他的书,这才是真正的纪念。对他灵魂的真正告慰。刚才听了西辞唱的《王小波1997》,唱得很不怎么样。歌词也烂,比如里面有一句把王小波和黄霑张国荣放在一起怀念。我觉得很不是滋味。我也喜欢黄和张,却不喜欢他们在这儿出现。
不管这首歌怎样,里面有两句话却触动了我,一句是“沉默的大多数”,另一句是“一个有趣的人”。事实上这两句话都在王的文章里出现过。他的那篇杂文名字就叫《沉默的大多数》。虽然我从小到大都不喜欢背书,但这篇我几乎可以背下来。
用“一个有趣的人”来形容王小波是最恰当的了,看过他的书的人都知道他的所有作品中都必须有幽默出现。而且这样的幽默必须善于思考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我记得清晰的一句话是他描写下乡时遇到的善良农民的走路姿态。他是这样说的:“只有一只板凳学会了走路才能走成这样”。莫言曾写过那个病恹恹瘦骨嶙峋但又有一种坚强精神的指导员时说:“像一具铁铸的鱼刺”。这两句话让我很久以来回味无穷。
我最爱的两篇杂文是《思维的乐趣》和《沉默的大多数》。前不久我们老师在课堂上讲杂文,这个老头拿着自己的一本杂文集给大家读,一边颇为自豪地讲解杂文的写法,讲着讲着他就不能自已起来,激动地说:“写得多好啊”。此时我差点像王二那样骂出一句脏话。我想天底下有那么多好杂文不讲,为何非要读自己那点拿不出台面的东西来毒害大家。我当时很想给他推荐王小波的一些文章看看,让他明白自己一生确实白活了。
王小波的一生是不平静的,可是在文坛里他又是最平静的。他最喜欢登山运动员解释自己为何要登山时说的那句话:因为山在那儿。对王小波来说写作也是如此,他觉得自己适合写小说。对于很复杂的想法用最简单的话回答是最有力量的。大半生都在学理,年近不惑却下决心辞了教授职位专心写作。这需要的勇气就不是谁能轻易理解的。我觉得人应该为了一些事纯粹而决绝的活着,当他感到自己该做某事时就应该不顾后果。
王小波在写作的那几年时时与乐趣相伴,与孤寂为友,远离文坛走向真正的自己。他一直是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我喜欢他说自己是沉默的大多数。我觉得自己将会和他一样。我想在价值观上我已经从他那儿学到不少。坚持纯文学的道路,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文章风格。
他说过无数次,不能容忍无趣。由此递进到不能容忍没有思维的乐趣。他说对于善良的人尤其应该警惕。特别是愚昧而善良的人。因此我们对愚昧深恶痛绝。“假设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是这样的,我常常被愚钝而善良的人弄得没有脾气。他们总是怀着一片好心使你无法拒绝那些强加给你的落后思想意识。从而破坏你的独立人格。
关于王小波的小说我想那就更加精彩了,我最喜欢的是《黄金时代》和《革命时期的爱情》。我喜欢他小说里的荒诞气息,正像卡夫卡一样,到处都是不可思议。到处都显示了文学的真正想像力。
1997年的那天深夜有人听到一声惨叫从某个窗口传出,这里住着一位大家不熟悉的人,或许是深居简出吧,在城市里某个不起眼的房间里写作是最容易得到平静的事了。第二天大家看到他痛苦地躺倒在地上,嘴巴贴在墙上,已经死去。直到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他叫王小波,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几个人把这个名字与文学联系起来。之后有三百多人自发参加他的追悼会,大家念他的《黄金时代》。只是这些人中竟没有一个知名作家,可见他与文学圈关系是多么冷淡。
王小波文章真正大红大紫是在他死后,有关这个现象我和王小波一样迷茫。生前他写了很多文章,经常收到退稿信,有时编辑还不忘借机在回信中挖苦一番。那时他说;文章的出版比写作要难上几倍。而就在他死后不久,他的文章却在市场上铺天盖地卷来。喜爱文学的在笑声和眼泪中阅读他的思辨性颇浓的文章,不喜爱文学的则津津有味地寻找一些性爱描写然后迫不及待地读下去。现在转眼十年过去了,人们又给他雕了裸体铜像。这一切表明了一位作家的真正生命力。
然而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怀念,作家自己或许并不因此而得到安息,他真正想要的或许是后人对他作品本身的理解。而我们真正要做的也只是好好读他的书。
版权声明:本文由我本沉默传奇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