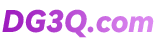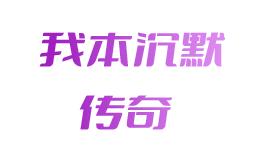
故乡的泉水
少小离家的时候,我不过是怀揣着憧憬和幻想的十几岁的翩翩少年,时隔多年,我由懵懂少年迈入中年,经过了许多是是非非,一直借口工作太忙,几乎没有时间回到渐渐疏远了的故乡,故乡的风物便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模糊。人
少小离家的时候,我不过是怀揣着憧憬和幻想的十几岁的翩翩少年,时隔多年,我由懵懂少年迈入中年,经过了许多是是非非,一直借口工作太忙,几乎没有时间回到渐渐疏远了的故乡,故乡的风物便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模糊。人到中年,经过了许多事情,看穿了许多人和事,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便少了许多,亲情、乡情触动了我麻木的神经,于是决定回故乡去看看。故乡在泸定县的12个乡镇中算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的乡镇,看到风景依旧,心中不免黯然,唏嘘感慨。在藏区,当看到有的农牧民已经走上了水泥路的时候,我所在的那个村子还是坎坷不平的机耕道路,汽车可以勉强通到家里,也算是“户户通”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该知足了。
让我激动的是山泉水依然欢快地从家门口流过,清澈得象少女的眼睛,我便急不可耐地俯下身子喝了一口甘冽的泉水,立即感到神清气爽,眼睛也明亮了许多,没有了酷暑难耐的感觉,吸入的空气便有了水果的香甜和花草的芳香,我不由得像贪婪的色狼般疯狂地呼吸着像少女体香一样的新鲜空气。
故乡的泉水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可能没有人能够考证了,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说,他还是孩童的时候,那股常年恒温、水量恒定的泉水就从他家后面不到100米的地底下缓缓流出,成为村民的生命之水。
如今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经寿终正寝,既然老爷爷都不知道故乡泉水的来龙去脉,谁还愿意去探寻究竟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人对哺育自己的这股泉水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我很小的时候,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村民粮食不够吃,公社社员一年到头起早贪黑,能够不饿肚子的人毕竟是少数。在农业学大寨的日子里,社员们积极性高涨,试图把荒山荒坡改造成良田,渴望都能够吃上大米。种水稻需要水,可地下水能够满足灌溉需要吗?在那个激情高于现实的年代,人定胜天的社员们终究没有圆吃上大米的梦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实施土地承包责任制犹如和煦的春风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科学代替了愚昧,代替了不切实际的狂热,先进种植技术的引进,故乡依靠地下泉水大量种植了水稻,故乡因此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水稻主产区,亩产量达到了一千多斤,吃大米已经不是什么奢望了。
地下泉水在故乡人心中是神水、圣水,象乳汁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乡人成长。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为了改变乡人的饮水质量,县上组织权威专家对地下泉水的水质进行了科学检测,水质标准令生活在城里的专家们艳羡不已,于是县上投资在地下水源地建造了两个偌大的水库,两根粗大的水管从水库蜿蜒伸展数公里,把洁净清澈的泉水输送到乡政府所在地以及乡上机关单位,于是故乡的地下泉水便有了极高的美誉度。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来故乡的游客不断增多,据说很多游客也许不会记住故乡的地名,却对故乡的泉水赞不绝口。夏天饮用清冽的泉水沁人心脾,十分惬意,冬天饮用泉水却没有寒冷刺骨的感觉,回味甘甜。用故乡的泉水烧开水,永远不会产生什么水垢,泡上家乡的茶叶,香气四溢,水香、茶香回味悠长,与其说是品茗,不如说是品味故乡的地下泉水。
我匆忙回了一趟故乡,物是人非的故乡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让我感动的印象,唯独这条常年流淌不息的地下泉水留在了我的梦里,滋润着我干枯的记忆和逐渐枯竭的文思。
版权声明:本文由我本沉默传奇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