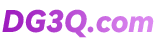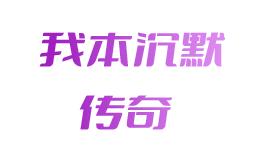
家,流动的驿站
在农村长大的我,总是会对老家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浓浓的乡愁,如同村西头那口永不枯竭的老井,给予我生命的源泉。记忆深处的某些东西,也时时缭绕在我的文字里,让我喜亦让我忧。
因为父亲的祭日,我回了趟老家。站在冷清荒芜的庭院,看到墙壁斑驳的老屋,想到人去楼空的凄凉,看到记忆中年轻健壮的左邻右舍,如今风霜已悄悄爬满脸庞,眼神中那隐约闪烁着的无奈……鼻子一酸,忽觉眼角湿湿的了。
跪在父亲的坟前,泪眼迷蒙,思绪如飞扬的纸灰,牵绊着我的哀思。大姑(父亲的妹妹)的哭诉,让人心酸。我知道大姑的哭,不仅仅是眷恋这份难舍的亲情,更是悲苦她自己的境遇。
姑姑年轻时就守寡。偏瘫多年的丈夫,留给姑姑的是高筑的债台,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儿子。生活的重压,一股脑儿地倾倒在这个身材单薄的农村妇女身上。
看着三个应该有媳妇了的儿子,姑姑更加省吃俭用。为了讨好村里的媒婆,姑姑没少揣着舍不得吃的鸡蛋,三把韭菜两把葱地往人家里跑。可是家里没个掌家的男人,有哪个女孩愿意呢?邻居的大叔可怜姑姑,主动与姑姑家合伙收种庄稼。可是,谁都知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呀,流言蜚语,让姑姑在村民和孩子面前抬不起头。看着邻居早已建起的窗明净几的大瓦房,自家低矮的茅檐,三个为媳妇急红了眼的儿子,姑姑想到了死。也许是喝了假药,也许是阎王爷的账本里,还没姑姑的名字,活过来的姑姑更加发狂地为儿子张罗着媳妇。
几年过去了,姑姑的两儿子,终于住进了饱含着姑姑辛酸乃至屈辱的大瓦房。姑姑继续与小儿子住在茅檐里,继续为小儿子的家打拼。我知道,新媳妇新婚不久,就会为结婚拉下的饥荒与姑姑闹得不可开交的。
在无人的夜里,姑姑的泪啊,流不尽。
姑姑的第三个儿子结婚,差一点让姑姑送了命。原本就很拮据的生活,让大儿子,二儿子的婚姻搜刮得所剩无几。小儿子长得帅气,有村里的女孩看上了,但是彩礼是一样都不能少的。亲戚们都被姑姑“借”怕了,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姑姑。为了儿子的新家,姑姑作出了一个决绝的行为——故意迎面撞上一辆疾驰的大货车。好歹司机很机敏,没有酿成大祸,姑姑为此遗憾了好长时间。可怜的姑姑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勒”人家一把,宁肯搭上自己的老命。
愚昧,可悲又可怜的姑姑噢。但是,作为一个母亲,除了稀嘘短叹外,我们还能责怪她什么呢?很早就听说过,可怜的父母们为了孩子上学,结婚,频繁地去卖血,但是,我的姑姑是在卖命啊。
最终,一个早年守寡的农村妇女,就这样用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身体,为三个儿子缔造了世间令人辛酸的“家”。
村里人,都说姑姑不简单,一个单身女人硬是把低矮的茅屋铸造成令她自豪的12间大瓦房。
辛辛苦苦几十年,姑姑的“家”在哪里?
后来听说,在村委会的调停下,姑姑轮流住在三个儿子家。姑姑说,暂住在儿子家的每一个月里,都感到是儿子家相对“贫穷”的一个月。我看到姑姑紧皱的眉宇里,流淌着岁月带给她的忧伤和无奈。
农忙时节,姑姑的家会一日“三更”。为了不引起三个儿媳的纷争,姑姑在一天中,尽可能均衡地为儿子家干活。就是这样,可怜的她也没让孩子们觉得把一碗水端平,抱怨责难还是向姑姑袭来。极度悲伤的姑姑,来到她丈夫的坟前,平静地诉说了一晚。姑姑没有眼泪可流了。
天亮了,姑姑踉跄着走出坟场,走向她晚年流动着的驿站……
女儿跟我说:姑姥姥就像一只疲惫的蜗牛,背着它重重的壳(铺盖),爬到这家,爬过那家。我无语而凝噎了。
其实,姑姑只是农村有些老人的缩影。
每当看到老家有老人去世,孝子贤孙们“以头抢地耳”的悲恸,过年时那被儿孙们神圣供奉着的先祖,都会引起我冷冷的思索。
在忧虑之余,我也欣喜地看到,很多村庄尊老爱老蔚然成风。农村老人的医疗养老任重而道远,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老人们会在一个“老有所养”的和谐国度里,幸福地安度晚年。
家,不再是老人伤心的驿站。我坚信!
版权声明:本文由我本沉默传奇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上一篇:这一日,即将毕业
下一篇:生命真的需要一丝丝的激情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