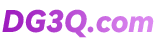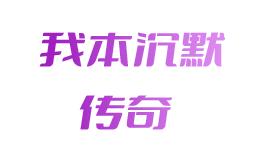
麦芽糖的味道
我的童年在乡村渡过,七十年代初的乡村和城镇物质都不是那么丰富,能吃上麦芽糖就是最甜最开心的事情。
秋收之后,拿出攒下来的上等谷子去粮店换了五斤小麦。小麦用来生麦芽。麦芽用来熬糖。
熬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生麦芽要技巧。麦子一粒一粒择干净,粒粒饱满。浸泡的时间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竹筛子洗净,铺一层白净的纱布,浸泡后的麦子均匀倒在纱布上面,然后盖上棉片遮光、提温。每日还得在揭开棉片往麦子上洒水,水也不能洒得太多。母亲日日洒水,我和弟弟日日看麦子一天天发芽。发芽的过程很缓慢,我和弟弟经常趁母亲不在的时候揭开棉片看麦芽有没有长到母亲比划的那么长。若是棉片没盖好,被母亲发觉,母亲的质问可是很严厉,弄不好要打手板的,因此,我和弟弟的窥视弄得很小心。
麦芽大月要一个多月才生好。生好的麦芽漂亮极了,嫩而成的芽,青里透着白,不,应该是白里泛着青,那样的颜色,是浑然天成的,是水粉和油彩调和不出来的。麦芽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光,仿佛春天就这么来了。麦芽晒上小半日,切细。糯米也泡好了,磨碎,放进大锅里煮。满满的一大锅糯米水,从清早点火,烧硬的干柴,一直要半夜才可以加麦芽,加麦芽要特别注意控制火候,边烧火,还要边在锅里搅拌。这个时候锅里的米汤只剩下半锅了,已经有了一点点颜色。换软一点的柴禾慢慢熬,直到米汤熬成浅褐色的糖,就可以起锅,熄火了。那个时候,我和弟弟早就等得迷糊上了床,清晨醒来,母亲陪嫁的瓷坛还是热乎的,揭开盖子,好浓郁的甜和香,真是馋得我们直流口水。这个时候母亲会满足我们的小小的欲望,差不多盼了一年,糖又熬了一天一夜。
熬糖需要大量的柴禾,并且还需要很多的硬的木柴,硬木柴烧出来的火劲才大,出糖才快,出的糖也多。我家挣的工分不多,分的柴禾少。父亲总有办法搞到硬柴禾。王家岗上年年伐树,树兜没人要,被父亲瞄上了。树兜晒干、劈开之后可是上好的硬柴禾。父亲一个周末可以挖上两三个树兜,推着鸡公车弄回家,大冷的天,父亲脱了棉衣,内衣都汗湿了。母亲见了父亲,露出她平日不多的笑容,我和弟弟很会察言观色,母亲笑了,晚上我和弟弟可以稍微轻松些,说不定还可以溜出去和队上的伙伴们到稻场上去玩赶山羊、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入了秋,我和弟弟对欢喜的事情就是到屋后的渠沟拾椿树枝。和弟弟比赛看谁捡得多捡得快,落在地上的树枝很快就捡完了。渠沟的椿树多,树枝自然也多。弟弟脑筋向来比我灵活,地上的树枝捡完了,弟弟使劲摇椿树杆,树枝顿然就落了下来。弟弟摇椿树,我在树下捡树枝。很小的时候,弟弟就以兄长的身份出现在我面前的,一来我是个丫头,在家说话不响亮,二来我喜欢生病,一年级开始弟弟长得就比我高。妹妹才学会走路,像个小屁虫跟在我们身后,她捡不到树枝,不哭也不闹,把我们堆在路边的树枝拨乱得到处都是,弟弟还揍过妹妹,妹妹哇着长大嘴哭。真是奇怪,我们姊妹三个,我和弟弟的嘴巴都非常的小,妹妹的嘴巴怎么就那么大,是不是与她动不动就撒娇、哭有关。
秋天完了,冬天来了。我和弟弟搓草绳,一捆一捆捆好树枝,父亲回来后再将它们码放整齐,椿树枝码满了我家的山墙。母亲却不表扬我们,还呵斥我和弟弟:“去年的椿树枝都没烧完,又捡回来这么多干什么,叫你们带好妹妹玩,还弄得她哭,眼泪水被秋天的风一吹,脸要嶒……”
椿树枝属于染柴禾,易燃,但比经烧,需要不断地添加。树枝在熬糖的过程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熬糖到了尾声,需要慢慢的用微火烧,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叫“熬”。
我和弟弟捡树枝无非是想母亲早点熬麦芽糖,麦芽糖熬好了,遇见母亲高兴,会奖赏我和弟弟一人一筷子,各自舔着缠了麦芽糖的筷子开心老半天。母亲称筷子搅的麦芽糖叫搅搅糖,一双筷子下去,得使点劲才搅得上。糖。母亲慢慢抽出搅上糖的筷子,再将两支筷子轻轻分开,扯出好长好长的丝。扯出来的糖丝越长,说明糖熬得就越好,越甜。母亲的笑和麦芽糖一样甜。
母亲喜欢把麦芽糖熬得老一点。嫩一点的麦芽糖颜色好看些,透明的亮,涔涔的黄,所以,也有人叫它“涔糖”。老一点的麦芽糖颜色深些,深褐色,也甜一些,但加的糯米和烧的柴禾多一些。在那时候的乡愁,我家的糯米和柴禾占得上一点点的优势,还是因为父亲的缘故。
麦芽糖可不是供我们搅着筷子舔的,要留在腊月尾上切米泡糖的。爷爷是切糖的高手,他会用最少的麦芽糖切上最多的米泡糖。进入八十年代,我十岁左右,爷爷切的米泡糖里面加了黄豆、芝麻,还有花生。我是十六岁离开老家的,离开之前的两年,爷爷给我家切糖,干脆不用米泡,纯粹的用芝麻、黄豆、花生了,不过,还是要稍微加点米泡才嚼得动,嚼得脆。
我们家切的糖有十板,要装一米坛。米坛有多大呢?就我家装米的瓦坛那么大,可以装五十斤米。我家米坛不装米,装切的糖。切的糖吃完了,米坛也空了,要空上至少十个月。那我家的米装在哪里呢?我家的米啊,装在柜子里的大菜坛里。
小时候的乡村过春节,走亲访友、拜年,米泡糖是招待客人的上等零食。七十年代的乡村,不是家家户户都熬得起糖,切得上米泡糖的,更不说是芝麻、黄豆、花生糖了。
姑婆家要几年才去一次。姑婆家里穷,父亲怕姑婆见了去拜年的我们窘迫,每次都选过了正月十五去给姑婆拜年。那年去姑婆家,姑婆家一片狼藉,准是和那孽障的儿子闹了架。姑婆见了我们自然高兴,手忙脚乱的,嘴里喃喃,说是没好东西招待我们。姑婆端出麦芽糖,我们姊妹几个来了劲,一个人一双筷子。弟弟力气大一些,搅上了一大坨,以为是一坨熬干了的糖,凑近看发现是只小老鼠,弟弟摔了筷子跑好远。姑婆眼睛不好使,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情。父亲见状,给我们自己做手势,意思是不要声张。那钵糖,按理是不能再吃了的,但父亲没出声,因为
版权声明:本文由我本沉默传奇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上一篇:三月“沪上百草园”之行
下一篇:《河流的声音》印象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