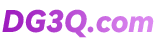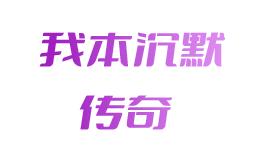
苇哨声声
前些天,村上人捎信说,苇生走了,死于矿难。送他那天,天是灰的,心是沉的。凄婉悲凉的唢呐声把我带回了遥远而迷蒙的童年。我的老家祁堂村,是中州大地上一个极为普通的村庄。她西边守着曲曲折折的贾鲁河,东边从北
前些天,村上人捎信说,苇生走了,死于矿难。送他那天,天是灰的,心是沉的。凄婉悲凉的唢呐声把我带回了遥远而迷蒙的童年。
我的老家祁堂村,是中州大地上一个极为普通的村庄。她西边守着曲曲折折的贾鲁河,东边从北到南是一条长长的谷地。谷地是河的故道,有几个大小不同的池塘组成。池塘里的水,常常随季节变化而变化,或多或少,但总是清澈透明的。水深的时候,人们在里面洗衣洗澡摸鱼,插科打诨的笑声伴着清风明月飘得很远很远;水浅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水底的杂草和飘落的枯叶,孩子们常在这里捉青蛙逮泥鳅,童年的乐趣深深地浸入了泥水之中。
在我的记忆里,每逢夏天,环村四周,水边岸上,长满了青青的芦苇。修长的芦苇紧紧地靠着,苇叶密密麻麻,形成了一道绿色的长城。微风过处,芦苇撩起靑纱,跳起优美的舞蹈;飒飒的和鸣与水中的蛙声,正好成了大自然美妙和谐的音乐伴奏。
每当这个时候,幽深的芦苇从中,时常会传出一两声“呜哇——”“呜哇——”的鸣叫。这鸣叫就是苇哨的声音,它是我们当年的集合号。“出来了!”“集合了!”。随着喊声,一个个倏忽麻利的身影,从窄窄的踩得光滑的小路尽头闪出来。清一色光脊梁,短裤头,苇竿枪。圆而尖、光秃秃的脑壳,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明亮。其中那个黑瘦黑瘦,高高的,细细的,长得像根芦苇似的,就是苇生。
苇生是我幼年的玩伴。比我大不了几岁,听说是他母亲收割芦苇时生的。那年月,生产队挣公分谁也不敢落下,孩子生在地里是常有的事,哪像现在人这么精贵,刚怀上还没有一点感觉,就吃保胎药营养药什么的,上班的请个假,不上班的干脆就在家休息了。
苇生家弟兄们多,他既不是头,也不是尾;家里穷,父亲身体不好,想管没有能力。苇生头脑聪明,身体灵活,常常下水摸鱼或树上掏鸟烧着吃。即便是这样,很多时候还得靠小朋友们接济。那时谁家都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劳力多了会好一些。我家有爷爷父亲母亲三个大老力,再加上我哥当时也能参加劳动了,家里相对好一些。有时看他饿极了,我就从家里偷红薯面窝头给他吃,他很是感激我。后来次数多了,被我母亲发觉了。母亲问我,我如实地说了,母亲叹口气,也没说什么。
苇生是个孩子王,小朋友们都服他。当然,让人佩服就得有拿得出手的两下子。苇生上树快,这是小伙伴们公认的。不欺负弱小,爱打抱不平,也是深得大家拥护的原因。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吹苇哨。
苇哨,是一种叫做“哑巴”苇子做的。据说,这种苇子学名叫做旱靑苇,是一种不开花的的苇子,它一般生长在低洼潮湿的水塘或河边。小时候我们通常认为它是未长成而夭折的嫩苇子。这种苇子干枯后没有通常的芦苇坚韧结实,苇竿较细柔脆带些褶皱,用手狠狠的一掐就断了。做的稍长,声音低沉厚重;做的越短,声音越是清脆嘹亮。如果用水浸泡一下,做的精致些,就是唢呐的秘子,也就是喇叭的发生源。或许其“呜哇——”“呜哇——”的声音有些像哑巴说话,我们家乡人都叫它“哑巴”苇子。
记得那时,村上正在盛演电影《沙家浜》。青青的芦苇荡正如我的家乡,小朋友们都非常喜爱郭建光。苇生就带领大家模仿新四军出入芦苇荡与敌人周旋斗争的情景,苇哨常常成了我们当时相互联络的信号。一旦“队伍”聚齐,苇生有时还煞有介事地仿照电影郭建光出场,唱上一两句:“芦花放,稻谷香,杨柳成行”“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岂容日寇逞凶狂”唱罢一阵掌声。接着,便是吹苇哨比赛。
苇哨比赛一般分两项。第一是比谁一口气吹的时间长,吹的声音响亮;第二是比谁吹得花样多,模仿得特像。比赛规则很简单,各人必须使用自制的苇哨。第一项常常是毫无悬念,苇生当之无愧的冠军。只见他先扎一个黑虎蹲裆的架势,然后猛抽一口气,身体前倾,慢慢上扬,直到昂起头苇哨朝天,已是掌声一片。他仍不罢休,最后还要来个摇头摆尾的动作,才算结束。
第二项倒是有挑战者。一个邻村唢呐世家的子弟芦笛,因在他姥姥家——我们村住,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当然有比赛资格。这下可就热闹了。一是芦笛的基本功好,二是芦笛的苇哨精致。比赛似乎不应该有什么悬念。芦笛一上场便先声夺人,吹了一段“百鸟朝凤”。其声音婉转悠扬,清脆明快,真可谓珠圆玉润,赢得了大家一片掌声。轮到苇生出场了,只见他先学几声狗叫,又扯两嗓子驴鸣。小朋友们齐声叫好,芦笛似乎有些得意,苇生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紧接着,又见苇生先来一个深呼吸,然后闭上眼睛,绷住嘴,头往后一仰。人们都以为他要装死。刹那间,只见他一手捏住鼻子,一手将苇哨对准鼻孔,摇头晃脑,哼哼哈哈的竟然弄出几个不同花样。小朋友们这次真是乐死了,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甚至有人趴在地上,半天才站起来。不用说这次赢家还是苇生。
往事如风。苇生早早的就辍了学,我也到外地求学去了。后来各自成了家,都在忙自己的事了。再后来,听说苇生为了养家糊口,挣大钱娶儿媳妇,下窑挖煤了。
故乡的芦苇早已不复存在,苇制品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所谓的池塘也变成了几个无水的大坑,生命似乎有些绝望。
记不清哪位大家说过,人其实就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生命的脆弱,让人悲伤而感叹。生命又是灵动的,一个个故事化作成长的情愫,融进我们的血液里,一起跳动。
多少天了,我时常在声声的苇哨中醒来,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青青的芦苇荡。苇哨是我童年真切而美好的记忆。
别了,苇生!别了,苇哨!别了,我的童年!
版权声明:本文由我本沉默传奇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