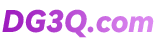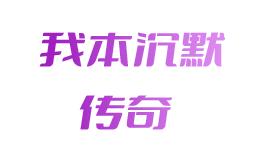
砖瓦厂记事
(一)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只要进会场或者会议室,很快就犯困,有时还瞌睡得要命,一离开那里,立马精神抖擞。按说要养成习惯,那就必须是好习惯,可我这坏习惯,就是一直克服不了。俗话说的好
(一)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只要进会场或者会议室,很快就犯困,有时还瞌睡得要命,一离开那里,立马精神抖擞。按说要养成习惯,那就必须是好习惯,可我这坏习惯,就是一直克服不了。俗话说的好: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在部队的时候,一次参加师政委关于人文知识的讲座,我怕打瞌睡,专门坐到了礼堂的最后一排,散场后被师政委叫住,问我他刚才讲的是不是不好?我赶紧说非常好,讲座期间一直掌声不断呀!师政委幽幽的说:看来掌声打扰了你的好梦呀!我尴尬的一瞬,赶紧解释说昨晚加班赶材料了……还有好几次,开会时我端端的坐着,忽然被旁边的人不时的推一下:被告知打呼噜了。
这个习惯可不行,经常在领导眼皮子底下,形象会大受影响不说,可能还会误事,一琢磨,想出一个法子:只要开会,瞌睡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本子上不停地写字,随心所欲,写啥画啥都行,一来赶走睡意,二来嘛,大家看到咱那样,还以为是认真的记笔记和领导讲话,看看!多认真呀!你别说,这个法子用陕西话说,那就是“燎滴太太”!
上周单位开会,我坐在最大领导对面,手中的笔划拉着,其间无意中看了不远处负责会议记录的小赵一眼:嗬!这家伙记录本下压着一份报纸,不忘了抽空看一眼,在她翻动的一瞬间,我这2.0的如炬眯缝眼只那么一扫,一行标题中的“瓦窑堡”三个字,一下子如同黑暗中的一个火星,瞬间点燃了我尘封的记忆,触发了年少时的岁月……
(如果你也有此习惯,我们是难友)
(二)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约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四、五岁的样子,好像是在一个冬天午饭后,雪花还在漫天飞舞,我应该是穿着母亲纺织的农家粗布做的肥厚臃肿而暖和的蓝、黑色棉衣棉裤,又穿着母亲亲手做的灯芯绒布----家乡人叫条绒布的棉鞋,鞋头有彩线绣织的小猫脸谱图案,还有两个圆圆耳廓尖尖耳顶的耳朵挺立在鞋头,很是活泼和卡通。那样的棉鞋在家乡司空见惯,家乡人唤着猫娃窝窝,现在老家的小孩也还有穿的。
我走出自家上房屋的大门,穿过天井,扑踏扑踏路过住在前屋的大伯家门口,看着前院被积雪覆盖的码放在土墙根的棉花杆和靠在墙上的玉米秆,有麻雀在雪地里和两树间拴着用来晾晒衣服的铁丝上飞落,通往巷道的院子中间已经被反复的扫过好几次,落上去的雪还不厚,我在坐二道门的石门蹲上,靠着门框一边看着雪景,一边左手拿小刀,右手握着半个已经冰冷的红薯,不时地割上一薄片或者一小块,刀尖叉着放进嘴里。那时候应该还流着清鼻涕,特别是寒冷的冬天。
踩着扫帚划过的痕迹,踏着虚虚的薄雪,我又来到大门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南北巷子,我一个人在呆立着。巷子里每家门前的雪都被扫过了,只不过扫的轻重、宽窄、频率不同。忽然,从巷子的北头传来了嬉闹声,是小孩子的那种无拘无束的吵闹和另一个孩子的哭闹。这种声音按说很平常,巷子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但这次,这样的声音刚一出现,立即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和注意,因为我觉得这些声音不同寻常,对我来说很是新鲜,以前从来没听到过。
准确的说,是传来的说话声嬉闹声和我听惯的当地的陕西话不一样,就像现在的人忽然听到外国人讲话、或者北方人猛地听到南方口音那样的不明就里。
很快,一大一小两个男孩,追打嬉闹着跑了过来,大的男孩比我大点,小的男孩比我小点,以前没见过。大男孩穿着蓝色的细布棉衣,棉衣的背带在脊背上交叉着跨过两肩,在两胸前黑色的大纽扣上扣着,大男孩的右胸前挂着厚厚的一个那种一页页能撕掉的旧日历,小男孩一跳一跳的去争夺那个日历,看起来是想要挂到自己身上,但他们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忽然,他们发现了我,立即安静下来,拉着手一边看我一边从我身边走过。这时候,后面的那个大人也走过来了,个子很高,走起路来好似脚底生风,走到我跟前的时候,笑着对我说了一句什么,但我听不懂说的什么,现在想来好像是问我叫什么名字。那个大人刚要摸我的头,吓得我一转身撒腿就跑回家了。
(如果你也有此经历,我们同龄)
(三)
故乡的村子有一个特点,每个村子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姓氏,村名就是以村子的姓氏命名的,比如我们的村子就叫柳家堡,临近有吕家堡、孙家堡、潘家堡等等,没考证过,不知道是从何年何月流传下来的,也不知何年何月这里开始形成村落,发挥想象猜测或者考证一下,大约也能推测出或壮观或凄美的故事。听一些老人讲,和明朝时期关中大地震后的大移民有关系。
再出去玩的时候,就看到了往日的玩伴中,多了几个新鲜的面孔,也就是冬日雪天看到的那两个孩子,不几日,又发现有一个更大的,是弟兄三个,夹杂在不同年龄的孩子堆中先是拘谨的,后来熟悉了,就开心的玩起来了。他们的口音,有一种让我好奇的腔调,听起来很好玩,时间长了,慢慢的也听懂了,他们的口音,慢慢的也被独一无二的陕西关中方言同化了。
这一家人,是从安徽某个地方逃难来的。听大人说,安徽的那个地方经常发大水,这一家人已经出来好多年了。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后来叫钢叔和兰婶的夫妇只有一个孩子,也就是老大方波。一路逃难乞讨颠簸谋生,在湖北的时候,生下了老二方澜;到河南的时候生下了老三方壮。到了我们村子没多久,老四出生了,取名方阔。等我后来上学后,语文学的多了,一次偶尔联想到钢叔他们一家子,我忽然内心不由自主的滋生出一种敬佩之心:这钢叔真是太有学问了,你看看人家给孩子取的名字:波澜壮阔!太波澜壮阔了!
我们的村子民风淳朴。钢叔一家到我们村子来落户,当时找到了队长,说明了情况,村里一合计,也不是什么难事,只是有一个条件:村子里有一个60多岁的孤寡老头,只要给老头养老送终,就没问题。钢叔一家立即就答应了。那老头人身材高大,但很和善,身体也很硬朗。自从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家庭,更是整天乐呵呵的。钢叔和兰婶称呼老头叫爸爸那是毫不含糊,他们的孩子那叫起爷爷来让人看了就像亲爷爷一样,真是其乐融融。
钢叔一家自然地成了村子里的一员,参加生产,操持家里,加上人很勤快,
版权声明:本文由我本沉默传奇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