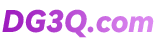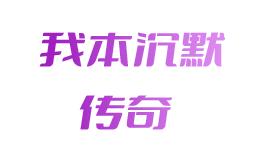
晓刚
弹指一挥间,离开生育我的故乡已近三十年。儿时的往事也如过眼云烟,在岁月的磨砺中日渐变得模糊起来,但那个和我同年同月出生的晓刚,却一次次穿越时空的隧道浮现在眼前。我们是在1968年9月出生在内蒙古敖汉旗
弹指一挥间,离开生育我的故乡已近三十年。儿时的往事也如过眼云烟,在岁月的磨砺中日渐变得模糊起来,但那个和我同年同月出生的晓刚,却一次次穿越时空的隧道浮现在眼前。我们是在1968年9月出生在内蒙古敖汉旗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里。那时正是国家的动乱年代,一片乌云笼罩着神州大地,轰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小刚那老实巴交的父母也难逃一劫。在小刚出生的前一个月,他的父亲遭人诬陷被赶进了牛棚。她的母亲也受到牵连,在他满月后被隔离审查。得不到母乳喂养的小刚身体极度虚弱,经常感冒发烧,好几次抽搐过去,险些丢了性命。虽在他奶奶的精心呵护下,他勉强活了下来,但还是留下一个后遗症,两手整天哆哆嗦嗦的。所以他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就像一颗营养不良的豆芽菜,面黄肌瘦、弱不禁风的。
我八岁那年,背着书包走进了学校。我的同桌就是晓刚,他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衣裳,光着脚丫,背着一个已褪色的花书包。消瘦的脸庞上透出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幅兴高采烈的样子。上课时经常有鼻涕流出来,他跐溜一声吸回去,再哆嗦着用衣服袖子一抹。那时我会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经典动作现在想来还记忆犹新,还想笑……
那时,我们全营子就一个学校,也就是生产队的三间破茅草房,全营子的孩子们不分年龄、年级挤在一间教室里由一个老师讲课。课桌是用木板临时搭建的,四个同学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听课,老师也是先给一年级讲完算术,再给二年级讲语文,如此循环。就这样,脏兮兮的小刚则显示了他过人的天赋,头脑聪明,记忆力好,加上他勤奋好学,一年的时间就学完了二年级的课程,成了同学当中的佼佼者,深得老师的赏识。等到第二年开学,他直接跳到三年级,把我甩在了后边。
当时,我们的课外活动也是枯燥无味的。根本没有什么体育设施,甚至连篮球都没见过。课外无非就是玩老鹰捉小鸡,打片子。而这些身材弱小的晓刚却很少玩,他经常玩那种“开河”“五虎联”等智力游戏,而且所向披靡,无人能敌,那些高年级的学生不服输,常联手和他作战,可翻盘的机会还是很少见的。最为佩服的是他会一种叫“韩信点兵”和“二十点”的游戏,不管别人有多少“兵”(都用石块或棒粒代替)只要把“兵”平均分成三组,晓刚把眼一闭,把“兵”都能分派出去,还有20个数字,不论你如何交换,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你手中的是几。当时对于我们那群孩子来说,那是神秘莫测的事情,都对晓刚怀有崇拜和敬意。为了和他学到这一手,我可没少给他溜须。
众所周知,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的生活相当贫困。我们生产队靠吃国家返销粮度日子。晓刚家因人口多,父母又有病,挣的工分少。家里经常吃上顿没下顿的,连棒面粥都喝不上溜。而我家人口少,我父亲又在外地工作,每月都拿着红本到镇上的粮站领回点粮食,所以棒面干粮我家还是常吃的,我每天都在书包里揣上一个,到校后送给晓刚。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另外,我还会把父亲给我带回来的《格林童话》《西游记》等书送给喜欢看书的晓刚,他就甭提有多高兴了。随之而来的是他的一些小技巧,小奥妙我总是第一时间知道,也成为了我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
这样一来二去的,我和晓刚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节假日里,我们一同上山砍柴,下河捉鱼,去树林掏鸟蛋,去田边捉蛐蛐……这时,跟在晓刚身后,都会有所收获,他能准确地判断那颗树上有鸟蛋,河里那里的鱼多,蛐蛐在什么方向。总而言之,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时光。
晓刚小学毕业那年,以全公社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中学,正当全营子的人都为他高兴的时候,一场噩运也随之降临了,她的妈妈在生他小妹妹的时候,因大出血在运往医院的中途不幸身亡。噩耗传来,晓刚是扑在妈妈尸体上哭得死去活来。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全营子的人无不落泪……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他妈妈前脚刚走,他的爸爸也患上了脑血栓住进了医院。这种打击对于一个花季少年来说,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一面要去医院照顾爸爸,还要看管家里的两个妹妹,(她的小妹妹在他妈妈去世后让她的小姨抱去喂养,)这一连串的打击过早地吸干了他身上的营养。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还未来得及开放就枯萎了下来,不仅让他的求学梦化为了泡影,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他整天沉默寡言的,起早贪黑拼命地干活儿……
就在那一年,我的爸爸把我们全家的户口迁到了他工作的地方,从此我离开了那个小村庄,走出了晓刚的生活,走出了我十二岁间的记忆。
星移斗转,岁月更迭,几千个日日夜夜悄然滑过。我在异乡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在高考时以较小分差与大学失之交臂。但我也算应验了那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我爸爸提前退休,让我接了班。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铁路工人,吃上皇粮,享受着国家俸禄。此后就接受了社会给我安排的习俗规范,为人夫,为人父。整天奔波忙碌着,日子虽然不富有,倒也衣食无忧,平淡而又幸福地生活着。
刚到异乡的时候,我还给晓刚写过一封信,不知什么原因他也没有回信。后因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极不方便,我们彼此间也就中断了联系。
直到十五年后,在我的婚礼上,老家的表叔千里迢迢来给我贺喜。从他的口中我又断断续续地了解了晓刚的一些情况。
晓刚辍学后,正值改革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一边伺候身患重病的父亲,一边照顾着妹妹,一边用稚嫩的双手和无尽的汗水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不分白天和黑夜辛勤劳作着,一年又一年播种着希望,风调雨顺之年,去了开支还有点剩余。可敖汉旗是个风沙狂虐、十年九旱的地区,我们所居住的村庄又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几年下来,晓刚的家也没有什么起色。未能摆脱穷困的束缚。
不肯向命运低头的晓刚清醒而又坚定地意识到:土里刨食是没有希望的,于是他找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筹了点款办了个小养鸡场。他的妹妹在小学毕业后看到晓刚日夜操劳、身心疲惫的样子,执意回到家中帮助哥哥,任凭晓刚怎么发脾气,生气,她都没有返校读书。
就这样,两年下来,哥俩办的鸡场也初具规模,日子也一天天好了起来。
版权声明:本文由我本沉默传奇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