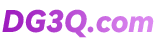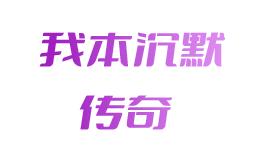
借书与买书
说到借书与买书,同样是读书人,偏好也各不相同。清代的袁子才说过一句极有名的话——书非借不能读也,历来被许多人奉为读书的圭阜。袁枚这话的科学性到底有几分,当然大可商榷,但毕竟算是他读书的经验之谈,加上袁本人又以诗文家和美食家而非藏书家闻名后世,所以推测他一生读书,恐怕多半还是以借阅居多,个人购书和藏书的量并不甚丰。否则,以他做过好几任知县大老爷的家底,如今的南京小仓山应该多少也能跟宁波天一阁别别苗头吧。与袁子才相映成趣的是湖南人叶德辉,叶德辉的名气虽然没袁子才大,但也决非泛泛之辈,此公在经学、史学、文字学、文学、考据、目录、版本等方面都大有成就,是清末民初可堪比肩王国维的大学者,也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叶德辉早年经商,发家后四处搜罗珍本古籍,辛亥革命那年,他在长沙坡子街的藏书楼观古堂已藏书二十多万卷,装满了一千多个书箱。叶氏爱书如命,曾在藏书楼的门上贴了张纸条:书与老婆,概不外借。一时传为笑谈。有时想,袁子才如果杠上叶德辉,肯定有趣得很——一个非借不读,一个打死不借。可惜两人前后差了有一百多年,关公终究战不成秦琼。
现代公共图书馆业发达,借书早已不是什么难事。去图书馆借书来看,既方便又经济,成为很多人的读书首选。象钱钟书先生,早年在清华就读时,借遍、读遍了半个清华大学图书馆,奠定了一生的学术底子。拿我自己来说,大学时读的一点书,也几乎全部来自于学校图书馆。记得那时,往往是在某人或某堂课上偶然听说了某书后,产生兴趣,于是转往学校图书馆按图索骥,这样做竟鲜有空手而返的时候,盖图书馆的藏书量实在够广够大。如此这般读书虽然不成系统,感觉却如同在书海里冲浪,爽快至极!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借书的感觉再怎么爽,也不可能全部取代买书。要说叶德辉、阿英、郑西谛那样的私人藏书家,日后恐怕终于不免会后继无人,但爱好买书者绝对不会绝种,这也是可以肯定的。否则,所有的书店现在开始就可以关门大吉了。一本明明已经读过或者图书馆很容易借阅的书,冲着心仪的作者、或者可亲的装帧、或者甚至某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铁了心非要买下来,如非同道中人,这种做法确实很难理解。其间的理由,马克思说得相当直白,甚至有些霸道,他说,书是我的奴隶,要为我服务!对书的占有欲,当是人类一切物质占有欲中的一种,只有掏钱买回家,这一本书,它才真正能算作你的“奴隶”,不用掐着指头细算还书日期,晨昏旦暮,枕席之畔,它随时听你差遣,随时供你亲近。难怪前人会发出“大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的感叹,拥书万卷,居然就有了类似做皇帝的感觉?我想说,一点不假,许多时候,这确是一切爱好买书者的真实感受呢。
当然,现如今爱好买书者也面临实际困难,主要有两点,其一,当代书生们普遍居室面积狭小、空间逼仄,书买回家后也没处放,稍不注意就容易积多成灾,拥书万卷的结果常常是满室狼籍,几无容脚之处。其二,书价奇高,一本书动辄售价三四十元,再看看自己可怜的工资单,热乎乎的购书之心立马就被浇冷了大半。总而言之,买书,似乎正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性消费,天可怜见!如此说来,好象倒还是借书来得实惠啊。
再转念一想,管它是借书还是买书呢,实在不成,网络下载也行啊,只需天天能有好书读,就天下太平万事OK了!
版权声明:本文由我本沉默传奇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上一篇:诚实的悲哀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