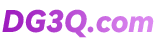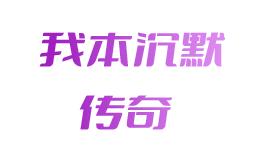
高雪萍对老报人邬明超的怀念
认识我的朋友,不免奇怪我怎么会以“高雪萍”的名字在汉网论坛出现?其实,这是我在黄石日报上唯一用过一次的笔名,她常常让我深深怀念曾在黄石日报担任过副总编辑的邬明超同志。1964年6月18日发表的《千里送
认识我的朋友,不免奇怪我怎么会以“高雪萍”的名字在汉网论坛出现?其实,这是我在黄石日报上唯一用过一次的笔名,她常常让我深深怀念曾在黄石日报担任过副总编辑的邬明超同志。1964年6月18日发表的《千里送来新文化》,结下我的黄石日报不解之缘。那年我是学生,黄石日报还不到12岁。后来,我当了老师,想通过写作提高自己,做一个合格的教师。于是在黄石日报的沃土上,先后发表了新闻报道、散文、诗歌、小说、评论、戏剧曲艺、音乐作品等,凡是中学语文里涉及到的现代文体裁,我几乎都发表过。即使“十年动乱“无稿费的日子里,我仍然乐此不疲。于是,未读过师范的我,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并在完中校长的岗位上退休。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中等微胖身材,黑黑脸上洋溢着温和的笑容的邬明超。
恢复高考的1977年12月,我就执笔了黄石的高考阅卷总结。1978年7月,黄石11039名高考生的阅卷总结,仍由我执笔。炎炎夏日,面临着教育政策、教育管理、教育现状的观察力和预见力的挑战,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拿出了总结。直到教育局高考负责人张德芳告诉我总结不错、领导满意后,我悬着的心才踏实下来。秋季开学后,我想把总结再加工变成铅字,让家长和社会能配合学校,抓好教育。毕竟总结里有全体阅卷老师的心血,于是借“高考学生阅卷评议“的谐音取了”高雪萍“的笔名。很快《一分为二话高考》的文章在1978年10月11日发表了,那年黄石日报26岁。
随后我接到熊编辑的电话,希望我到报社来一下,邬明超同志要找我聊聊。见面时,邬明超同志高兴地说:“文章反响很好,对中学教育有见地,希望你多写写这方面的文章。”事后,熊编辑对我说:”你这篇文章得了副刊的一等稿费,这样的事不多。“使我意外的是,邬明超同志还承担了责任。原来,文章发表后,他的一位华师中文系校友、教育局的中层领导,对文章的题目和发表程序提出了异议。当时的政治环境没有现在这样宽松,邬明超同志明确告诉校友,题目并无不可,作为个人投稿也是可行的;如果有责任,与作者无关。
我得到过邬明超同志的表扬和保护,也挨过他狠狠的批评。我有一篇理论方面的文章,先通过邮局寄到报社。两个多月没见报,正好这时有位编辑到铁山采访,我把稍作修改的同篇呈给他。他看后认为可以带走。此后仍未见报,我有些奇怪。不久,我到报社碰到邬明超同志,他狠狠地批评了我,说:一篇稿子送给两个编辑,两个编辑都发了,我到底采用谁的?这不容易引起误会吗?我不能发,不管你的稿子写得怎么样!今后,你再也不能干这样的事情了……。
小住京都的我,怀念邬明超同志,他始终把作者当朋友。我怀念为人随和却对稿件严格的副刊组长胡敬夫,怀念满面笑容的唐开云,怀念不放过一个病句的周崇涛,怀念朝气勃勃的熊编辑,怀念工科出身的晁芳,怀念一字一句修改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的殷春树……。我怀念这些黄石日报20多岁时的老报人。虽然,和他们有几十年不曾见面了,有的已经永远无法见面了,但他们保留着黄石日报平易近人、把作者视为知己的传统作风和美德,永远洋溢在我的心头,让我始终感受着那种温馨和亲切!
版权声明:本文由我本沉默传奇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