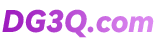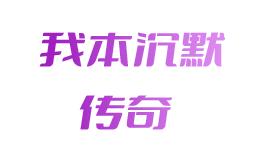
心疼一个女人
当我的手指有些犹豫地敲下这几个字时,我的心里却立刻鼓足了勇气,像是要决意叩开一扇陌生的门,去拜访一位仰慕已久的朋友。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北方的农村度过。冬季的乡下,躲在厚厚白雪下的村落,显得格外干净、寂寥、温馨。尤其是当一两声鸡鸣犬吠打破沉寂,一缕缕炊烟袅袅升起,你就会感叹大自然的造化之工、神来之笔,是如此神奇地将朴实的生活,融合到一种意境悠远的画卷中。站在清冷的晨风里,心里涌动着暖意。故乡的美,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就永远深藏在了心底。我想,当年萧红弃家临走之时,最后一次回眸远望,铭刻在心里的或许就是这幅美丽的画面。因为《呼兰河传》,便是从冰封的土地上长出的一棵奇葩,冰骨清奇,清香怡人。
罗马罗兰说:“岁月流逝,人生的大河中开始浮起回忆的岛屿。”其实,这些岛屿如同颠簸在汪洋中的诺亚方舟,只能使人暂时摆脱现实,逃避烦恼罢了。我想,在颠沛流离中求索的萧红,会不会在累了的时候,也静坐下来,去捡拾遗失在岁月尘埃里的那些记忆的碎片。她细心地擦拭它们,拼凑它们,用最温情的想象修复它们,使它们明亮起来,生动起来,幻化成最富有魔力的文字,为我们娓娓讲诉呼兰河的故事。
地处黑土地的呼兰河,是否还依然在流淌。生活在河畔的人们,是否知道一个叫萧红的女人,用最后一抹生命的光亮,将这条普通的河,印照在许多人的视野里。呼兰河在歌唱,轻柔徐缓的旋律,轻轻地萦回在《呼兰河传》的字里行间。
我惊异于在那个朝不保夕的战乱年代,一个人该有怎样纯净的内心世界,才有勇气和能力去还原这个世界本来的美。困苦的生活使萧红不堪重负,但黑土地、呼兰河赋予她的灵性使她的笔触细腻委婉,空灵传神。于是她用文字的颜料为我们绘制多彩的画卷,许多生活化的细节和自然景象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曾在小学课本中学过的《火烧云》,就选自《呼兰河传》。那一段文字色彩丰富,动感十足,于繁复的变化中又跳跃着音乐的律动,使人感受到一种希望和生机。古老的汉字,记述历史,但更多的是传承精神。精神的力量总是支撑人去求索,去进步。
茅盾在为《呼兰河传》所作的序中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但在我看来,它也是一面放大镜,虽清晰地展示呼兰河的生活风貌,却更深刻地暴露了国人的劣根性。萧红深得导师鲁迅先生的文法精髓,虽有女性的温婉,看似轻描淡写,只一个大泥坑,便让三六九等的人,都显了本来面目。其实,那样的泥坑在北方的农村很常见,那样的故事也不新鲜,但它存在的时间那么久,存在范围那么广,多少便有些耐人寻味了。
读其书思其人,是许多人的毛病,我也不例外。读《呼兰河传》时,我在心里常常描摹萧红的神情容貌。该像《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敏感聪颖,但却没有她的尖酸刻薄;该像薛宝钗的宽宏大度,但却没有她的圆滑世故;该像史湘云的的率性坦荡,但却没有她的粗陋疏狂。但萧红自己说,她是苦命的香菱,在男人面前煎之熬之的香菱。
2009年第一期《散文》上,耿立的《临终的眼:萧红》,为我讲述了萧红的归宿,叹惋之余,甚感惆怅。抗争时的决然,顺受时的默然,同样的令人震颤。原来,萧红更像一株柔弱的藤萝,她倾付真心柔情,只想依偎一棵坚实的大树,哪怕是嶙峋的岩石,风雨共担,荣辱与共。但最终,她却在孤苦无依中,寂寞地离开了这个世界。1942年1月,年仅三十岁的萧红,在香港病逝。
现在已经是春天了,绿的汛潮已然在辽阔的原野上汹涌。当我把目光投向窗外,黎明的曙光像一把巨大的羽扇,正轻轻地拂去夜的残片。那轮红日就要喷薄而出,阳光的飞瀑将倾泻而下,清洗每一个劳碌的身影,冲刷每一寸厚重的土地。那就请照耀那一方矮土吧!温暖那个让人想起就心疼的女人。
版权声明:本文由我本沉默传奇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